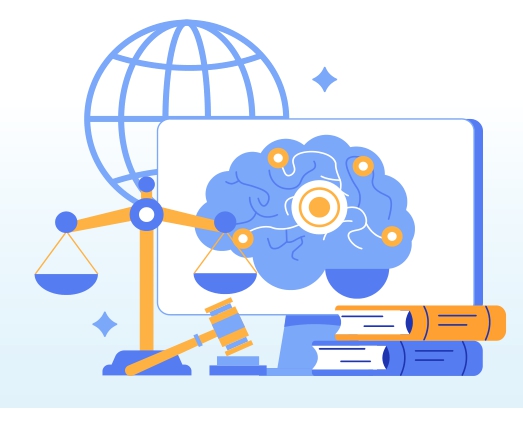
当前政策为脑机接口技术发展提供了沃土,产学研医等各方需要沉下心来,用稳扎稳打的技术突破和严谨的临床验证推动产品落地,让这项技术真正造福患者
□ 本报实习记者 常锐博
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公布了其最新研究成果:目前已有7位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包括4名脊髓损伤患者与3名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患者。数据显示,这些受试者通过脑机接口产品,能够玩游戏、控制机械臂写字等,重获与物理世界交互的能力。
上述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直接带动了我国脑机接口概念股的走高。
事实上,我国在脑机接口研发领域也是成果斐然,今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等地多个科研团队均取得进展。
不过,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表示,作为一项前沿技术,脑机接口研发应用还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投入,更需耐力。
发展驶入快车道
所谓脑机接口,是指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信息通道,实现两者之间直接信息交互的新型交叉技术,可应用于军事航天、工业安全、医疗康养等多个领域。
“在医疗领域,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脑机接口有望为中风、婴儿脑损伤、痴呆症、癫痫和孤独症等传统诊疗方法难以应对的脑神经系统疾病,提供有效的治疗途径。”赵继宗介绍。
赵继宗介绍,全球脑机接口研究已开展近30年。与加拿大、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脑机接口研究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已与国际水平接轨”。
经过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国内多个科研团队相继公布成果:
1月,上海脑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脑虎科技)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微系统所),分别为运动区和语言区占位肿瘤的两名癫痫患者植入256通道柔性脑机接口,术后两名患者成功实现意念控制游戏、AI大模型对话等操作。
3月,南湖脑机交叉研究院联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等单位,为一名完全性截瘫的患者植入脊髓刺激电极,术后的2个月内该名患者运动功能有所恢复。
6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等科研团队也分别开展了脑机接口产品的临床试验。
伴随着科研团队的持续攻关,资本市场对脑机接口给予了无限热情。公开资料显示,全球脑机接口行业的投融资活动在2020年进入活跃期,截至2025年2月,全球脑机接口领域投融资事件超过1500起,总金额接近100亿美元;其中,我国投融资事件超过200起,总金额接近20亿美元。
IT桔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脑机接口领域共发生投融资事件9起;其中,上海阶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2月获得的3.5亿元B轮融资,是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行业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融资。
不仅如此,入局这一领域的企业也越来越多。根据智药局在今年3月份的统计,我国脑机接口企业数量增长至34家;华为、腾讯等也着手布局这一新兴领域。
面临技术、伦理等多重挑战
作为一项前沿技术,脑机接口研发面临着多重挑战,如基础理论不够、技术尚待突破和伦理不容忽视等。
目前,脑机接口按照获取神经信号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两类。其中,侵入式脑机接口因其可获得高质量的神经信号,临床应用场景更为丰富。
但大脑是神秘且复杂的器官,由约1000亿个神经元组成。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家对大脑高级运作机制的研究仍较为有限。“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神经信号编码原理和脑机交互机制的基础研究。”赵继宗说。
此外,对侵入式脑机接口来说,如何实现电极材料的创新和系统集成的优化,是目前技术层面的一大挑战。
南湖脑机交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跃明介绍,按照材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电极大致可分为刚性和柔性两种。刚性电极植入操作简单,但长期植入可能对大脑组织产生一定伤害;柔性电极与大脑相容性更好,但植入难度比较大,“最为理想的电极是兼顾二者优势”。
据悉,目前国内一些团队在积极探索研发刚柔可调电极。王跃明研究团队研发的该方面产品已进入动物试验阶段。
系统集成是脑机接口技术面临的另一大挑战。脑机接口是集电极、芯片和算法于一体的精密系统。要开发高性能脑机接口产品,不仅要求单个组件性能优异,还需要实现整个系统的高通量处理能力。
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周志涛介绍,仅就电极或芯片而言,目前的技术已经能达到上万的通量。然而,要想将这些组件集成到同一系统中,现有技术很难在确保高通量以获取高质量脑电信号的条件下,平衡系统的体积与功耗,并同时满足临床植入对设备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严格要求。
此外,脑机接口的研发和应用还涉及复杂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认为,在脑机接口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要确保技术应用不会对身体和大脑造成永久性伤害。其次,由于该技术还可能对使用者产生主体性改变,包括意识干预、行为习惯重塑等,需要对产品进行严格的伦理审查和风险评估。而在社会伦理层面,相关研发则涉及更为复杂的数字权益争议,如精神完整权和数据共享等。
还有专家认为,脑数据是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如何防止数据泄露、滥用,以及确保使用者的知情权和自主权,也是这项技术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多方接力跑好长赛道
毫无疑问,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必然是一场长跑。
周志涛介绍,其研究团队自2016年开展脑机接口技术基础研究工作,经过近10年的前期技术积累,才具备根据临床需求研发相关产品的能力。
然而,产品的研发只是第一步。要实现产品的注册上市,还需要经过型式检验、大动物试验、大规模临床试验等科学验证。“对于前期技术积累扎实的企业来说,从产品定型到最终获批上市,如果一切顺利,通常需3~5年时间。”周志涛表示。值得关注的是,每个环节中都伴随着技术的迭代优化。
面对这场长跑,赵继宗表示,“政产学研医”的多方接力不可或缺。
据悉,2024年9月以来,国家药监局已批准脑机接口相关的多项医疗器械行业标准立项,包括术语定义、测试方法、数据质量要求及评价方法等。
今年7月,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关于发布优化全生命周期监管支持高端医疗器械创新发展有关举措的公告》专门提到,将配合相关部门出台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医疗器械产品支持政策,持续健全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等新型生物材料标准化研究体系,并加快推进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医疗器械安全性有效性系统评价方法研究工作。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发布《神经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其中专门为脑机接口新技术价格单独立项,设立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费”“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出费”等价格项目,为相关产品临床使用打通了通道。
相关的伦理审查体系也在完善过程中。2023年10月,科技部印发的《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要求,对包括“侵入式脑机接口用于神经、精神类疾病治疗的临床研究”在内的7类科学活动开展伦理审查复核。之后,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人工智能伦理分委员会编制发布了《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进一步细化了脑机接口研究的伦理规范要求。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北京、上海、四川等省份陆续出台支持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
“当前政策为脑机接口技术发展提供了沃土,产学研医等各方需要沉下心来,用稳扎稳打的技术突破和严谨的临床验证推动产品落地,让这项技术真正造福患者。”赵继宗说。
延伸阅读
脑机接口关键技术和潜在应用场景
近年来,脑机接口领域快速发展,其在关键技术及典型应用场景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
脑机接口的关键技术正处于加速突破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电极柔性化趋势显著。例如,Neuralink开发的1024通道高密度柔性电极Threads已完成多例临床植入;哈佛大学开发的超柔网状电极有望长期稳定记录单个神经元信号;Axoft采用超软脑植入材料Fleuron™研制的探针已完成首批人体临床试验;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了蚕丝蛋白电极等柔性电极。
芯片向多功能集成一体化、微型化发展。例如,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发的高精度记录-解码SoC芯片,以超低硬件资源实现复杂信号解码;Neuralink的植入芯片Blindsight,集成了电极阵列,兼具多功能和体积较小,可绕过受损的眼睛和视神经生成光幻视信号,有望帮助视神经损伤或先天失明者恢复基础视觉能力。
微系统集成化取得重大突破。例如,Precision Neuroscience开发的第7层皮层接口,兼具高通量薄膜电极阵列和微创手术植入系统,通过“颅骨微缝”新技术,即可完成快速、微创的硬膜下植入;Paradromics研发的高速率脑机接口产品Connexus可记录1600多个独立神经元信号;清华大学牵头研制的无线微创植入脑机接口NEO仅有两个1元硬币大小。
脑机接口在典型场景的临床应用不断拓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在感知觉增强领域,南加州大学研制的超声视网膜假体完成动物试验,未来有望以低损伤方式恢复视力;复旦大学研制的碲纳米线网络视网膜假体和暖芯迦开发的视觉脑机接口,均验证了临床转化潜力。
在运动功能重建领域,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利用脑深部刺激技术让瘫痪患者恢复独立运动能力;南湖脑机交叉研究院通过闭环脊髓神经接口植入手术,实现截瘫患者自主站立、行走等多种日常活动;Neuralink全植入微型脑机系统让瘫痪患者通过意念完成游戏和3D设计任务。
在脑疾病治疗领域,Medtronic研发的脑起搏器,用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等疾病;杭州青石永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研发了针对抑郁症的神经刺激器,发展了靶点选择、参数优化、闭环调控等技术,截至今年7月,已开展40例急性、3例长期IIT研究;佳量医疗研发的植入式自响应神经刺激系统,截至今年6月,已完成近80例多中心临床试验。(王跃明)